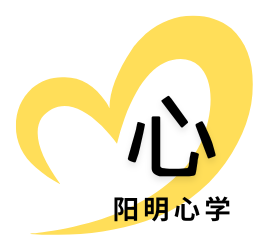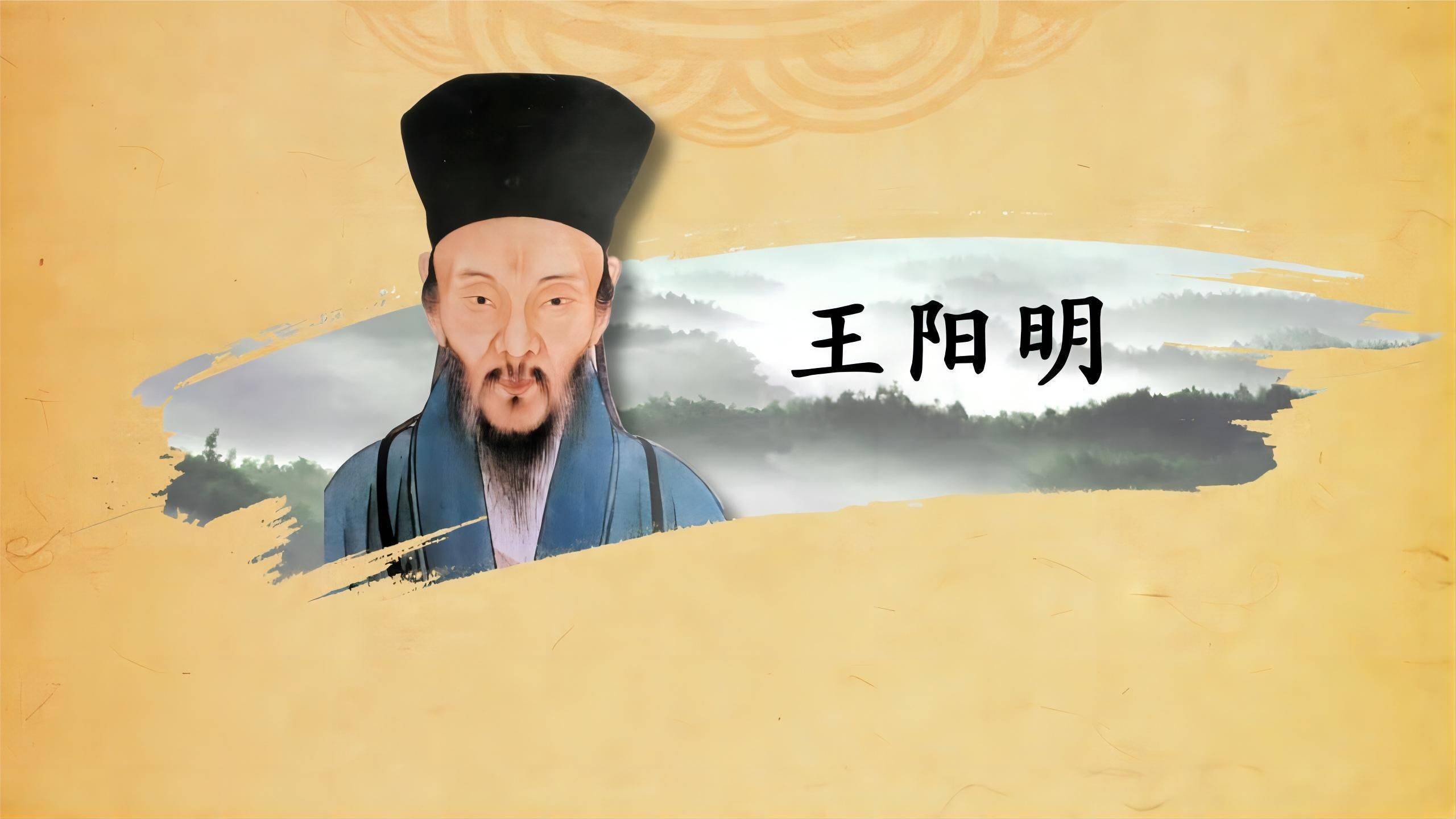正文
屡得弟辈书,皆有悔悟奋发之意,喜慰无尽!但不知弟辈果出于诚心乎?亦谩为之说云尔。
本心之明,皎如白日,无有有过而不自知者,但患不能改耳。一念改过,当时即得本心。人孰无过?改之为贵。蘧[qú]伯玉,大贤也,惟曰“欲寡其过而未能”。成汤、孔子,大圣也,亦惟曰“改过不吝,可以无大过”而已。人皆曰:“人非尧舜,安能无过?”此亦相沿之说,未足以知尧舜之心。若尧舜之心而自以为无过,即非所以为圣人矣。其相授受之言曰:“人心惟危,道心惟微,惟精惟一,允执厥中。”彼其自以为人心之惟危也,则其心亦与人同耳。危即过也,惟其兢兢业业,尝加“精一”之功,是以能“允执厥中”而免于过。古之圣贤时时自见己过而改之,是以能无过,非其心果与人异也。“戒慎不睹,恐惧不闻”者,时时自见己过之功。吾近来实见此学有用力处,但为平日习染深痼[gù],克治欠勇,故切切预为弟辈言之。毋使亦如吾之习染既深,而后克治之难也。
人方少时,精神意气既足鼓舞,而身家之累尚未切心,故用力颇易。迨其渐长,世累日深,而精神意气亦日渐以减,然能汲汲奋志于学,则犹尚可有为。至于四十五十,即如下山之日,渐以微灭,不复可挽矣。故孔子云:“四十五十而无闻焉,斯亦不足畏也已。”又曰:“及其老也,血气既衰,戒之在得。”吾亦近来实见此病,故亦切切预为弟辈言之。宜及时勉力,毋使过时而徒悔也。
译文
屡屡收到弟辈来信,都表达了悔悟前过、发奋进取的决心,真是无比欣慰!只是不知诸弟果真是出于诚心呢,还是仅仅是口头说说而已?
本心的光明,犹如白日一般明亮,没有人有了过错自己却不知道的,问题在于不能改过啊。一念改过,当下便能回归本心。人孰无过?贵于有过能改。遊伯玉是大贤人,他只是说:“欲寡其过而未能。”成汤、孔子,是大圣人,他们也只是说“改过不吝” “可以无大过” 而已。人们都说:“人非尧舜,孰能无过?”这也只是一种沿袭的说法而已,人们并没有真的明白尧舜的心。如果尧、舜的心里真的以为自己没有过错,那他们就不会成为圣人了。尧、舜一脉相承的心传是:“人心惟危,道心惟微,惟精惟一,允执厥中。”他们自己也认为人心惟危,那就说明他们的心也和常人是相同的。“危”就是过错,尧、舜唯有兢兢业业,曾经用过“惟精惟一”的功夫,才做到了“允执厥中”而免于过错。古代的圣贤能时时自见己过并加以改正,因此能做到无过,这并非是他们的心真的与常人不同。“戒慎不睹,恐惧不闻”,就是“时时自见己过”的功夫。我近来真见到了此学问的用力之处,但自己平日积习太深,克除改正却欠缺勇气。所以我真挚地预先提醒诸弟,不可如我一般,一旦习染已深,再想克治就难了。
人在年少之时,不但精神意气易被鼓舞,而且没有养家糊口之事累心,所以易于用功学习。等到渐渐年长、世俗的牵累日渐加重,精神意气也逐渐衰弱,不过,如果此时还能发奋努力,则尚有成就的机会。但是,到了四五十岁,人的精神意气衰微更甚,就像下山的太阳,光明慢慢微弱熄灭,大势已去。所以孔子说“四十五十而无闻焉,斯亦不足畏也已。”又说:“及其老也,血气既衰,戒之在得。”我近来真切地感受到了这个问题,所以才会提早对诸弟切切提醒,你们应当及时发奋努力,不要等错过了大好时光而白白后悔。
背景简介
1518年,正德十有三年戊寅,阳明先生四十七岁。《寄诸弟书》是阳明先生写给自己的弟弟们的一篇文章。在这篇文章里面阳明先生着重讲了改过。言语直接,古之圣贤时时自见己过而改之,是以能无过。劝诫弟辈们改过不吝。
施邦曜在《阳明先生集要》一书中就此文有评曰:“人能自见其过,必实实能下克己功夫,方能觉得。若只外面虚谈性命,张说名理,未有不自以为是者。所以夫子曰:‘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。’盖难之也。指点克治真切功夫,无逾于此。”